陸穎墨小說集《小島》:講述鮮為人知的西南沙水兵故事

陸穎墨,當代軍旅作家。江蘇常州人。曾獲魯迅文學獎、當代文學獎、中華文學選刊獎、小說月報百花獎、小說選刊年度獎等各類文學獎三十余項。著有《海軍往事》《尋找我的海魂衫》《白手絹,黑飄帶》《中國月亮》《遠島之光》《軍港之夜》等。短篇小說《小島》被收入教育部統編《語文》教材,另有作品《潛浮》《歸航》《遠航》等收入各種中小學語文教輔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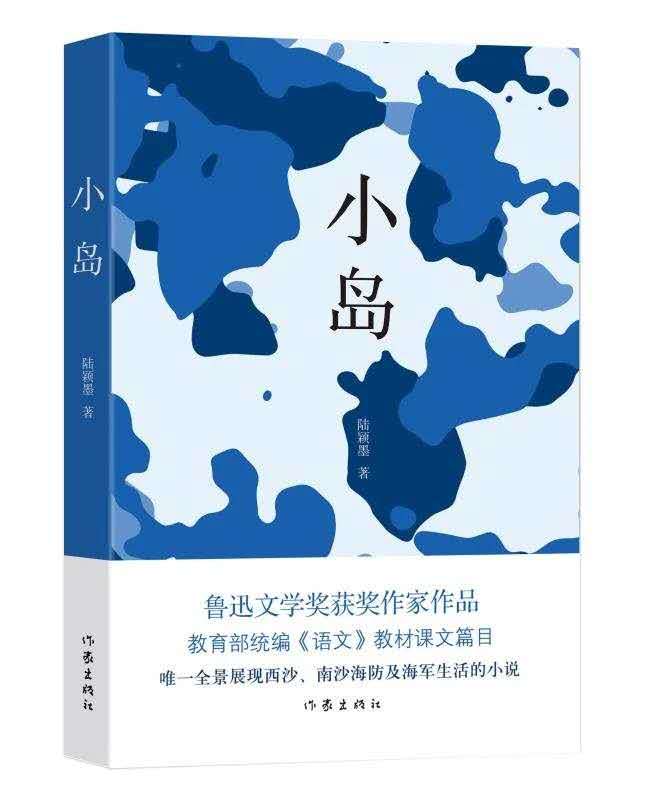
小說集《小島》 陸穎墨 著 作家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1990年,陸穎墨第一次遠航去西沙。那天,船外涌起數米高的巨浪,形如一排排藍色的大山,他暈船暈得一塌糊涂。第二天風浪減小,他看到很多海鷗跟著軍艦飛,便問水兵:“為什么海鷗一直跟著我們的船呢?”水兵說:“幾百公里的海上看不到一個島嶼。如果海鷗飛不動了,跌到浪里就得淹死。在遠海的時候,它必須跟著船。”陸穎墨當時第一個想法就是,在連海鷗都生存艱難的海面上,我們的水兵戰士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默默堅守、無私奉獻,用生命守衛著南中國的藍色國土,捍衛著國家的和平。那次遠航給了他很大觸動,也影響了他的寫作。很多年來,陸穎墨一直凝望著那片遙遠的南中國海,用文字記錄、講述水兵的生活。近日,中國作家網記者采訪了作家陸穎墨,聽他分享小說集《小島》背后的創作故事。
記者:你從什么時候開始創作的?為何會選擇創作軍旅題材的作品?
陸穎墨:我是1984年從軍校畢業,1986年開始寫小說,1987年在《當代》發表了小說處女作《軍法在戰前執行》,自此走上文學道路。讀書時,我不斷積累關于海軍和海洋方面的知識,這是我寫海軍題材小說的原因之一。那時候,我對海軍官兵的真實生活了解不多,直到工作后走進部隊,漸漸才有了更深的了解。小說集《小島》里有一篇小說《錨地》,寫了軍艦海上錨訓的故事,錨訓是艦艇部隊的一種訓練方法,錨訓時,軍艦要駛離碼頭,在離海岸不遠處拋錨訓練,艦上的人可以看見陸地,卻不能上岸,這樣一訓就是一兩個月。艦長老周的妻子前來探望,只能遠遠站在岸邊看軍艦“尋找”老周,她的深情凝望以及特殊的表達方式感染了我,后來就寫了這篇小說。由于這則真實故事的發生地是在南海部隊,在那里一時形成了很好反響,許多官兵都把自己家稱作“錨地”。還有一篇《歸航》,寫的是軍艦在南海上遭遇強臺風被裹入臺風中心,左右猛烈搖晃,海面上時不時會傳來一陣陣發出悶聲的滾地雷。滾地雷是南太平洋特有的“怪物”,沿著海平面亂竄,一般的避雷裝置對它沒用。小說里的這些場景和細節,包括小說主人公肖海波對此作出的判斷“順著臺風中心走”,是有真實原型的。生活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力。
記者:您的小說《金鋼》里寫到:“島上濕度大,腿關節染了嚴重的風濕……所有人在礁上都要戴著護膝;還要穿長袖,要不穿長袖,南沙的紫外線兩小時就會讓你脫層皮”;《小島》提到了“島上蔬菜缺乏……出海時會暈船,還會遇到神秘莫測的‘土臺風’,淡水資源也缺乏”。這些環境描寫在小說里多次出現。這都是海軍戰士面臨的具體困難。
陸穎墨:隨著不斷關注和接觸,我對堅守在一線的海軍戰士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敬佩。他們駐守在西南沙島礁上,很長一段時間生活環境很艱苦,如果沒有親身去過那里,很難真正體會到。實際上,海軍官兵面臨的困難要比小說里描寫的多。他們堅守崗位,守護著祖國的南大門,將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安危連在一起,默默作著貢獻,甚至犧牲。這份默默的堅守中有一種自我價值實現的崇高感和使命感。上世紀90年代我在西沙島遇到了一個剛要退休的工程副總指揮,他當時對我說,“當了一輩子兵,能趕上在西沙建這么重要的工程,軍旅生涯這個句號畫得太圓滿了。當了幾十年和平兵,退休前轟轟烈烈干這幾年,以后在兒孫面前可以吹個幾十年。”后來,我把他的這些話寫進了話劇,用作臺詞。都說守衛在遙遠島礁上的水兵是英雄,其實我更愿意將他們視作普通人。這些年輕的軍人來自四面八方,大多是二十歲上下的小伙子,不少還很稚嫩。但是在特殊的環境中,愛國之心將他們內心的英雄情懷激發了,點亮了,他們的意志也逐漸剛強起來。他們的生活鮮為人知,我希望民眾對他們多了解、多理解,并對他們懷有深深的敬意。
當然,現在他們的生活環境得到了很大改善。海軍的海上補給能力明顯增強,蔬菜的保鮮技術也有了提高。但是由于南中國海的自然環境異常惡劣,海軍官兵們的生活還是非常艱苦。
記者:小說里寫不少關于海洋關于西南沙地理方面的知識,讓人覺得很新鮮。你能從這方面再介紹一下嗎?
陸穎墨:海軍是國際性兵種同時又是綜合性兵種,包含著水面艦艇、潛艇、航空兵、陸戰隊以及岸防部隊等多個兵種。由于技術密集、專業分工多,除了過硬的身體素質和心理素質,中國海軍對邊防海軍的知識儲備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潮汐漲落對軍艦的靠泊都會有影響,有的時候海上施工要搶退大潮的時間。再比如水下施工,潛水兵必須長時間在海底作業,提前把地形勘探清楚,如果在海底需要水下爆破時,就要把炸藥安放精準,實際上困難很大,存在很多技術難題,海流、海浪等因素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問題,還有一定的危險。
我們的軍艦經常出訪、援外以及進行亞丁灣護航,面臨的涉外問題比比皆是。如何按照國際慣例巧妙處理這些問題,對官兵們提出很高的要求。軍艦在日常巡航中也會遇到各個國家的軍艦,有時還會遇到挑釁,指揮員們必須顯示出高超的軍事能力和外交能力。在當下,博士艦長已經不算新鮮了。
記者:小說里的許多人物都帶有英雄色彩,比如《歸航》里的肖海波,更多的還是真實呈現海軍官兵身上那種豐富細膩的情感,《艦橋》里江偉和賀毅的戰友情,《遠航》里肖海波和肖遠的父子情,《錨地》里老周和他妻子的夫妻情,也包括《白丁香》里實習護士許淼淼對軍港水兵那種樸素的情誼。小說中這種情感特別飽滿,充滿感人至深的力量。
陸穎墨: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并沒有刻意去呈現這種情感,但我本人是充滿深情的。你覺得作品文字情感飽滿,也許和我長期的生活積累、寫作習慣以及對海軍官兵的了解和體驗有關。我覺得我一直在努力地同他們的內心世界建立聯系,關于之前的《海軍往事》,有讀者跟我說,《長波》寫了“誠”,《遠航》寫了“愛”,《彼岸》寫了“義”,《艙門》寫了“勇”,我想想還真是那么回事。小說雖然是虛構的藝術,我一直在努力尋找內在的真實,捕捉、挖掘、展現海軍官兵作為普通人的那種真實的狀態,因為只有真實的生活和情感才能打動人。
在寫之前,我總試圖把自己的情緒調整好。對我來說,寫一篇小說時,把第一句寫完,然后在第一段找到定位,其實整部作品的敘述腔調和風格特征基本上就確定了。比如《遠航》這篇小說,我本來想以宏大敘事開始,開頭就這樣寫:“西昌艦要開始它最后一次遠航”,但感覺有點“大”。后來就改成了“西昌艦要走了,是最后一次”。我把敘述對象西昌艦當成了自己的戰友,距離一下就拉近,敘述的感覺就不一樣了。
有人說,這些小說顯現出來的情感體現了一種向往美好的力量,有理想主義的色彩,但故事情節和人物塑造又很真實,在現實世界中有跡可循,實際上是“現實主義里帶有理想主義的色彩”。
記者:這本小說集幾乎沒有寫愛情。《白丁香》寫了朦朧的情感,但不能算愛情。
陸穎墨:《白丁香》寫了護士許淼淼和軍港兵的珍貴情誼,那不是愛情,就是兩個不到二十歲的小孩子之間一種樸素真摯的情誼,主要還是想展現海軍戰士作為普通人身上的那種真實情感。有一個評論家說《白丁香》寫了社會上一種比較稀缺的情懷,比如人與人之間那種溫暖的、珍貴的情誼,很感染人。這本小說集很少出現女性,幾乎全是正面描寫剛硬堅強的士兵,以及他們之間超越功利性的戰友情。對我來說,生活確實是我的創作之源,幾十年的軍旅生涯積累了豐富的海軍生活,我自己才情有限,生活的豐富彌補了這個短板。也有人認為我的小說有些粗糲,不太文藝。其實我也想“文藝”,后來覺得放在自己的作品里不是那么回事,許多作家朋友也有同感,于是我放棄了“文藝”,堅持自己的粗糲。
記者:小說《金鋼》里多次出現“國旗”這個意象,如:“每一個守礁士兵回大陸時,都會得到一面換下來的國旗”。如何理解這句話?
陸穎墨:我認識一個軍官,守礁三個多月期間,寫了大量的日記,記錄守島生活的點點滴滴,包括執勤巡邏、種植蔬菜、收集雨水等。守礁回來,他還給我展示了一件寶貝:一面被海水打過、太陽曬得發白的五星紅旗。他告訴我,完成守礁任務后,都能得到一面發舊的、帶著故事的五星紅旗。我無數次仰望飄揚的國旗,但那面國旗,卻是第一次見到。后來,有一年,我又看到另外一面被猛烈臺風撕裂了邊角的、同樣來自南沙的國旗。帶回這面國旗的是另外一位年輕軍官,他在南沙執行任務一百多天,到過好幾個礁盤。國旗在他們心中占據很高的位置,與他們有著深刻的聯系,每一面國旗都有故事,都有滄桑的壯美。
其實關于國旗,還有很多動人的故事。按照國際慣例,軍艦是移動的國土,哪怕是大洋彼岸,升有五星紅旗的軍艦就表明這是中國的領土。記得人民海軍軍艦第一次到美國訪問時,華僑上艦參觀,一位白發蒼蒼的臺灣老兵,流淚親吻夾板,說幾十年了終于親到了祖國的土地。這種情感,沒有經歷很難體會到。有一年,我去西沙執行任務,返程前突然遭遇臺風,歸期未知,當時立刻覺得自己被拋到天邊。那一瞬間,對大陸的思念潮水般涌上心頭,我一下理解了那些駐守島礁的官兵為什么對祖國大陸懷有那么深厚的情感。
記者:小說《潮聲》里出現的“電報”也是這樣一種意象。
陸穎墨:《潮聲》的靈感,來源于兩件事。一是,那一年我在島上過年,會餐期間,聽到一個士兵問隊長,今年過年的電報是不是快來了?隊長說,來什么來?還輪不到我們呢,發到南沙去了,那邊最遠。當時聽來就是一種普通的對話,卻覺得其中蘊含著很深的情感。又有一次,我們單位的一位年輕軍官要去南沙代職守礁,臨行前,我提醒他寫日記,把這段難得的經歷記錄下來。一周后,我接到他從礁盤上打來的電話,當我在北京聽到祖國最南端傳來的聲音的時候,那種感覺真好。之后,他幾乎每隔三五天就打來電話,突然有一周音訊全無,一問,線路壞了。過了幾天電話又打來了,他說這周把他憋壞了,電話線連著,總感覺和祖國大陸連著;電話線不通,心里突然就空落落的,覺得大陸特別遙遠。后來,我就寫了小說《潮聲》,以對話形式推進小說敘述進程,也寫了守礁士兵心情的復雜性,一方面有因電報遲遲不來的些許失落;另一方面,也有為祖國海防的強大感到欣慰自豪。
記者:軍犬對士兵來說,也是戰友,甚至《升騰》里的兩枚導彈,田水直接給它們命名為“大懶”和“二懶”,在導彈發射之前,有一部分文字描寫可以體現出他對這兩枚導彈的感情:“田水一下子呆在那里,沒想到,明天自己的手指一按上發射鈕,它們就要和自己永別了。他覺得喉嚨發緊,慢慢地,田水走過去,緊緊地挨個抱住它們,淚水,無聲地流了下來。”
陸穎墨:軍艦出航后,軍艦上的每一個士兵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如果是一艘深潛于海底的潛艇,更是如此。他們身處不同的崗位,甚至都可能看不到彼此,但他們是一個整體,肩負著共同的責任和使命,面臨著共同的困難。一艘軍艦、一個潛艇,關系到好幾百人的生命,每個人堅守好各自的崗位,整體才會發揮出最大的優勢,而整體的成敗既關系到軍人的使命任務也關系到個人的安危。這些讓他們緊緊聯系到一起,成為“命運共同體”,感情深厚。
記者:從篇幅來看,28個短篇小說,除了《金鋼》《艦橋》《白丁香》一萬多字,其余25篇都在五千字以內,有的甚至更短,比如《小島》《遠航》《潮聲》《通道》《橡皮》等,三千字左右。
陸穎墨:我個人更愿意從結構上劃分,而非字數。其實,從篇幅來看,目前還沒有對短篇小說的確切定義,我們現在通常所說的小小說字數在2000字以內,超過這個字數,就是短篇小說。在寫《小島》《遠航》《潮聲》等小說之前,我已經寫過一些較長的小說,包括一萬多字的短篇小說,甚至,字數更多的中篇小說。后來參加《解放軍文藝》雜志社在南京組織的一個關于精短小說的筆會,給了我一些思考。當然寫作不是單純為了長而寫長,為了短而寫短,一篇小說的價值也從來不以字數的長短而論,字數少不會拉低作品的質量,相反,對寫作者而言,不長的小說,要把它寫好,其實更難。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工作也越來越忙,分不出太多時間和精力寫篇幅長的作品,我寫得又比較慢,總喜歡修改和打磨,寫完后把每個字再讀一遍,凡是我認為多余的部分都要把它去掉,哪怕是一個詞語、一個字,盡可能“做減法”,盡量不用成語。我曾經開玩笑說,我肚子里沒有太多詞匯,語言也是大白話,小學五年級就能看懂,沒想到十多年后一篇小說還真成了五年級課文。
記者:這種精短文體和你的閱讀有沒有關系?
陸穎墨:上學時,我看長篇小說多一些。新時期以來,我非常愛讀《人民文學》,也經常看《小說選刊》《新華文摘》等選刊;《當代》《小說月報》給我寄了三十年,一直是我出差途中的伴侶。閱讀國外的小說主要集中在一些短篇上,比如歐·亨利、莫泊桑、阿爾豐斯·都德的短篇小說,其中都德的《最后一課》和莫泊桑的《項鏈》,包括歐·亨利的《警察與贊美詩》《最后一片樹葉》等對我的影響比較大。這些小說篇幅都很短。我一直覺得,作品篇幅的長短其實是根據需要而定的,比如我寫的篇幅較長一點的《白丁香》,一萬三千字左右。我一直想把它寫短,但《白丁香》確實沒法寫短,因為要表現兩個陌生人之間那種純真的情誼,要讓他們在結尾“握手”,前面一定會有大量鋪墊,否則小說的邏輯性就會受影響,失去張力,很難說服讀者。
記者:您的短篇小說《小島》被編入教育部統編的《語文》教材課文里。
陸穎墨:這篇作品最早在2008年被編入湘教版語文教材六年級下冊,當時的題目叫“礁盤”。2012年,國家啟動統編教材的編寫工作,改成《無名島》被編入教育部統編的《語文》教材五年級下冊,2019年6月正式調整到五年級上冊。經過教材委員會審查,《無名島》改名為《小島》,因為全國的島嶼很快都要有自己的名字。還有其他一些小說被收錄在各類教輔教材中,多數被用作閱讀理解。特別有意思的是,《金鋼》這篇小說去年10月在《人民文學》才發表出來,到年底好多中學已經把它節選為期末考試題。看來海軍題材作品還是挺受人歡迎的。
記者:最近有開始創作新的作品嗎?
陸穎墨:我寫得慢,還是寫海軍題材,手頭正在寫一篇《金鋼》的姊妹篇,暫名《海底叢林》。題目的意象來自海面下的一大片珊瑚礁。


